從我國的汗青文明傳統看“地下偷竊說”在我國不可行。“盜”在先秦曩昔是不分行動體式格局的,而是抽象地指侵占財富一類的犯法。有學者指出:“偷竊一詞,在先秦文獻中常見,是秦漢曩昔侵占財富罪的概稱”。寶山刑事律師告訴您相關的情況是怎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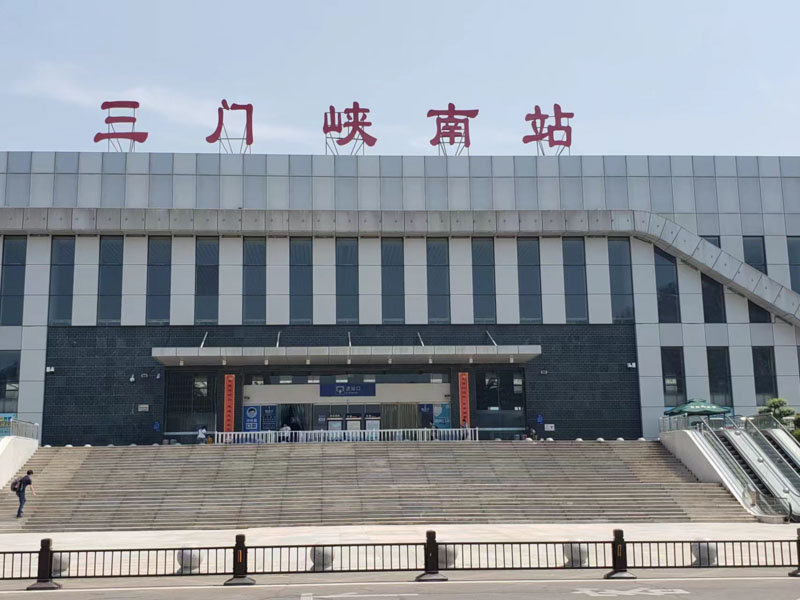
此后,“盜”逐步被區分為種種范例,如群盜、竊盜、匪賊等,此中,“竊盜”便是隱秘盜取的意義,起初“竊盜”又演化為“偷竊”,也便是當今意義上的偷竊。《晉律注》最早明確區分了“盜”的分歧范例,此中“竊盜”便是隱秘盜取財物的犯法。
自唐律起,立法上劃定了較為翔實的分歧范例的“盜”罪。唐律《賊盜律》劃定:“諸盜,公取、盜取皆為盜”。由此可見,唐律中的“盜”是指以地下或隱秘的體式格局非法獲得別人財物的行動,詳細分為匪賊與竊盜。自唐朝起,相干的學理說明都稱盜竊罪應具有隱秘性。
唐律對于偷竊寄義的界定間接被《宋刑統》《大明律》和《大清法規》所承繼,《大清法規統考》“響馬窩主”第18條劃定:“凡盜,公取、盜取皆為盜。公取,為行盜之人公然而取其財,如匪賊掠奪;盜取,謂潛行碰面而私竊取其財,如竊盜掏摸,皆名為盜”。
“偷竊”作為“盜”的一種體式格局,是隱秘取財,這在現代立法以外的文獻中也能失掉證明。“竊”,據《說文·通訓定聲》說明:本意為蟲私食米,蟲私食米不容易為人發覺,引申為乘人不知而獲得非分食品。明清時代的學理說明也都將竊盜解釋為隱秘取財,《大清律輯注》將“竊”解釋為“乘人所不知而暗取之”;將“盜取”解釋為“畏本家兒之知覺,潛蹤隱跡,私竊而取之”。
北洋軍閥時代,盜竊罪的劃定基本上相沿了《大清爽刑律》。國民黨統治時代,舊中國最高法院1933年上字第1334號判例指出:“搶奪罪,系指悍然牟取而言。若乘人不備盜取別人所有物,并不是出于公然奪取,自應構成盜竊罪”。

新中國成立后,1979年《刑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均贊同盜竊罪具有秘密性,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當前辦理盜竊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都規定“秘密竊取是盜竊罪的重要特征,也是區別其他財產犯罪的主要標志”。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承認盜竊罪具有秘密性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貿然放棄這一歷史文化傳統進而承認“公開盜竊說”顯然缺乏正當性,因而是不可行的。
隱秘盜取是盜竊罪的基礎特性的觀念在我國擁有悠長汗青文明傳統,跟著社會的不息進展,盜竊罪擁有隱秘性被不息強化,盜竊罪與搶奪罪的邊界也日漸清楚。大眾所說的“明搶暗偷”便是對搶奪罪夸大悍然性而盜竊罪夸大隱蔽性的精準歸納綜合。
本日,假如踐行“地下偷竊說”,那會極大地打擊普通大眾和法律職員的傳統法令觀點,下降大眾對刑法的認同感。應當抵賴,我國刑法學通說注意盜竊罪擁有隱秘性、搶奪罪擁有悍然性,而且其對于盜竊罪與搶奪罪的區分在法律實踐中并未暴露出顯然的題目。
堅持我國刑法學通說關于盜竊罪與搶奪罪的界定,既有利于保持司法的穩定性、延續性,也符合民眾的預期。雖然每個國家的盜竊罪有相同之處,但是受歷史、文化傳統、刑法理論、國民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各國對盜竊罪的含義及構成要件的界定可能會有所不同。就我國而言,堅守我國刑法學通說,堅持盜竊罪具有秘密性,應該說是符合我國國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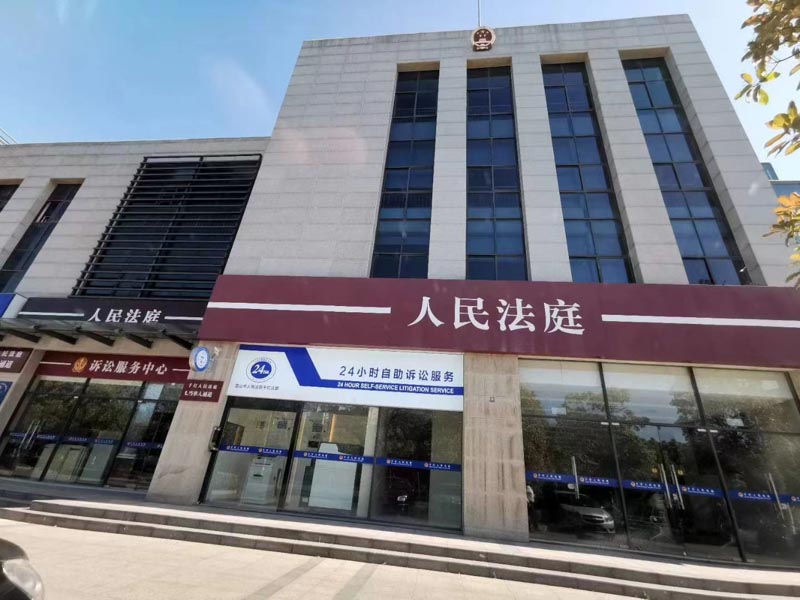
正如寶山刑事律師所言,一種規范論的刑法教義學,要重視解釋者個人的先見,更要重視解釋者群體的經驗,要讓解釋結論符合實踐理性的要求,使解釋結論建立在不可辯駁的法律基礎之上。我國學者對盜竊罪的解釋也應該如此。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