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刑訊逼供之外,究竟哪些非法取證方法可以或者說應當納入“等”字所指范疇,具體判斷和認定的標準又該怎樣理解和把握皆是問題。在本案中,被告人章國錫曾辯稱:偵查機關在偵辦案件的過程中嚴重違法,采用了疲勞審訊以及威脅、引誘、欺騙等手段獲取其有罪供述。上海專業刑事律師為您講解一下有關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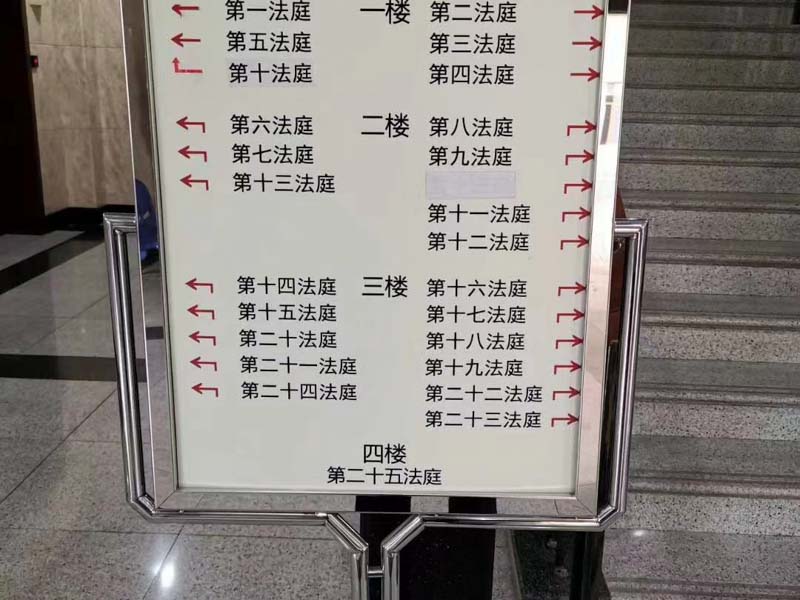
那么,“疲勞審訊”是否應納入“等”字所指范疇予以禁止?而偵查機關通過威脅、引誘、欺騙性手段獲取證據又是否應一律認定為以非法方法取證?
第四,程序問題。也就是說,程序如何排除非法證據?如果被告申請排除非法證據,舉證責任如何分配?在控方承擔舉證責任的前提下,辯方是否也應分擔部分舉證責任?控方如何證明所獲證據的合法性?如何把握案件的證明標準?
第二,概念問題:是缺陷證據,還是非法證據在本案一審程序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曾辯稱:2010年7月22日10時左右,被告人章國錫被反貪局偵查人員控制,當時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因而是非法的。但顯然,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主張與法院在判決書中的認定存在一定差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認為,偵查機關的前期偵查行為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因而構成違法偵查,所收集的證據也構成非法證據應予排除。而法院在判決書中僅認定偵查機關的前期偵查行為存在瑕疵,所形成的證據為瑕疵證據而非非法證據。
從證據法理上講,“瑕疵證據”不同于“非法證據”。首先,在性質上,“非法證據”系偵查機關以嚴重侵犯人權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而“瑕疵證據”雖同屬偵查機關以違法方法獲取之證據,但違法程度較輕,并未嚴重侵犯公民人權。
形象地說,“非法證據”屬于不可原諒之“大錯”,而“瑕疵證據”則屬于可原宥之“小過”。其次,在效力上,“非法證據”自始即無證據能力,一經查實即應從程序上予以排除。而“瑕疵證據”則屬于效力未定的證據,是否有效取決于該證據的瑕疵能否被補正或合理解釋。
若瑕疵證據的瑕疵經補正或合理解釋而消除,則瑕疵證據可轉化為合法、有效的證據,具有可采性;若瑕疵證據的瑕疵無法補正,則該證據將轉化為無證據能力的證據,不具可采性。我們注意到,在本案審判過程之中,法官并未徑直將偵查機關的前期偵查行為定性為違法偵查行為,而是一再要求控方對證據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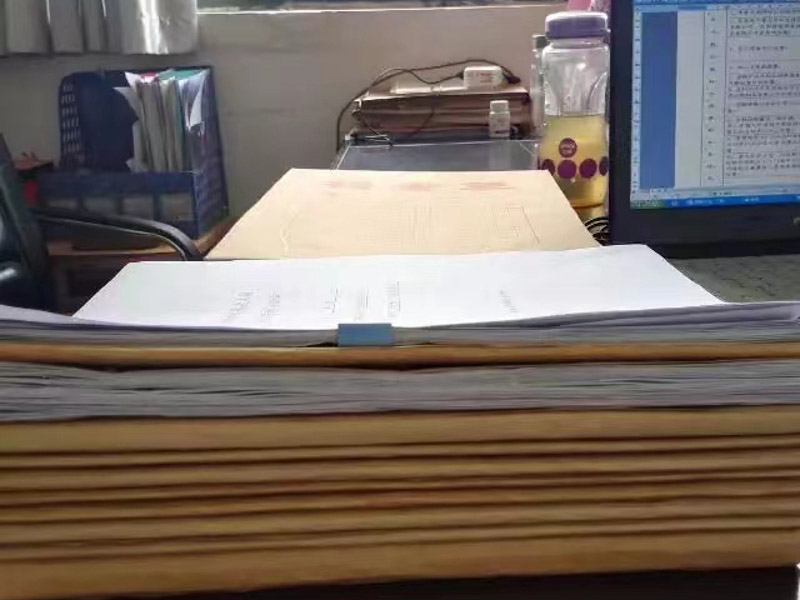
這表明,法官更傾向于認定偵查機關的前期偵查行為雖然具有違法性,但尚不足以構成非法取證,只要控方能夠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法官仍愿意采信該證據。只是因為控方始終無法向法庭補充提交東錢湖紀委找章國錫談話的筆錄或其他證據以證明紀委《情況說明》的真實性,無法消除證據的瑕疵,法院才最終否定了上述證據的效力。
問題是,法院的上述判決和裁定是否正確?從證據法理論的角度來看,在這種情況下,偵查機關通過前期調查形成的證據究竟是非法證據還是有缺陷的證據?筆者認為,上述問題的答案必須逐一界定,找出以下問題。
首先,本案的前期進行偵查工作行為影響究竟是紀檢監察管理機關的違紀學生調查研究行為,還是中國檢察監督機關可以實施的初查行為?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國對于紀檢監察行政機關通過調查以及辦案并無需遵守國家刑事訴訟法關于公司立案、偵查等相關法律程序之規定與要求,因而,若本案前期偵查活動行為是否屬于我們紀檢監察審計機關根據調查辦案,檢察機關僅僅是一個協助,那么就無所謂違法的問題。
但是,在本案庭審過程中,雖然控方向法庭提交了東錢湖紀委的《情況分析說明》,試圖證明本案前期偵查犯罪行為系紀檢監察機關對章國錫違紀情況的調查社會行為。

上海專業刑事律師發現,由于控方無法向法庭補充提交東錢湖紀委找章國錫談話的筆錄或其他證據以證明紀委《情況具體說明》的真實性,法院系統最終得到否定了該證據的效力。因此,本案的前期市場調查結果行為能力應從實質上解釋為檢察機關的初查行為。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