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要件(Tatbestand)是整個犯罪論體系的基石范疇與核心意念。盡管從古典派的犯罪論體系到新古典派的犯罪論體系,以及后來的目的主義的犯罪論體系與目的理性的犯罪論體系,構成要件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重大的嬗變。然而,構成要件的基本功能并沒有廢棄,它仍然是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的基礎。蘇俄刑法學從一開始就把構成要件轉換為犯罪構成,而犯罪構成是犯罪成立條件的總和,因而四要件并不是建立在構成要件基礎之上的,我稱之為沒有構成要件的犯罪構成。本文擬從構成要件的理論出發,對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進行批判性考察。
一、構成要件一詞是費爾巴哈首先引入實體刑法的,因而從刑法學的立場出發,一般都把構成要件理論的源頭追溯到費爾巴哈。那么,費爾巴哈是在什么含義上使用構成要件一詞的呢?對此,俄國學者指出:費爾巴哈只把犯罪行為的客觀要件歸入Tatbestand中,而把主觀屬性(罪過)排除在犯罪構成要件之外,將它們看作是犯罪人負刑事責任和具備可罰性的第二個(除Tatbestand之外)獨立的條件。由此可見,在費爾巴哈那里,構成要件是指客觀的構成要件,并不包含行為人的主觀要件。構成要件的概念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傳入俄國,但沙俄刑法學接受費爾巴哈的構成要件概念以后,對其加以廣義的理解,從而形成主客觀相統一的構成要件的概念。
俄國學者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指出:19世紀中葉,俄國的刑法學家接受并將Tatbestand引入到了學術用語中,這個詞譯成俄語后就是犯罪構成。這樣,這一問題(以及其他問題)就“遷移”到了俄國的刑法理論中。Tatbestand在學說中被廣義地解釋為一定數量的必要的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不能增加,亦不能減少。對于十月革命前沙俄時期對構成要件的研究狀況,特拉伊寧明確指出:革命前俄國的著作,對犯罪構成問題也很少關注。在俄國革命前的刑法著作中,沒有關于犯罪構成的專門書籍或專題研究。
與此同時,特拉伊寧又指出:前面已經指出,俄國革命前的刑法著作,對于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沒有予以很大的注意。但是,不能不指出,在俄國的著作中,卻把犯罪構成作為主、客觀因素的總和,作了比較深刻的論述。特拉伊寧對十月革命前沙俄學者對于犯罪構成研究狀況所作的評價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說“很少注意”,另一方面又說“作了比較深刻的論述”。如果我們把“很少注意”的犯罪構成看作是犯罪構成的一般條件,而把“作了比較深刻的論述”的犯罪構成視為是犯罪成立的具體條件,則以上困惑可以迎刃而解。在沙俄時期沒有形成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未能將犯罪構成當作一個專屬概念進行體系性的建構。但沙俄學者對犯罪成立的實體條件作了較為深刻的論述,并且這些犯罪成立條件是包含了主客觀條件的,只不過沒有納入犯罪構成的體系中加以研究。例如,特拉伊寧在論及沙俄學者H.C.塔甘采夫沒有研究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時,引用了塔甘采夫的以下論述:
同任何法律關系一樣,犯罪行為的重要要件可以歸結為三大類:
(1)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人;
(2)犯罪人的行為所指向的東西——侵害的客體或對象;
(3)應當從形式上和實質上受到審理的犯罪的侵害行為本身。
在此,塔甘采夫勾劃了主體——客體——行為這樣一個結構,而這一結構正是從法律關系的思維方法中引申出來的,即法律關系的主體、法律關系的客體和法律關系的事實本身。
我國學者曾經引述塔甘采夫的以下論述:作為對實際存在的法律規范的侵害、對法律所保護的生命利益的侵害,犯罪是產生于侵害者與侵害對象之間的某種重要的關系,它本身包含獨有的特征或要件,并以此為根據構成一般類型的法律關系,并且該類法律關系中犯罪作為刑事的可罰的不法而占有一席之地。這些說明犯罪行為要件的總和在刑法科學中,特別是在德國學者的著作中被稱為犯罪構成。在此,塔甘采夫明確地把侵害者(主體)、侵害對象(客體)與侵害行為并列,而犯罪構成只不過是說明犯罪行為的要件總和。由此可見,這里的犯罪構成雖然已經包含了客觀要素與主觀要素,但仍然不是犯罪成立條件的總和,因為犯罪主體與犯罪客體尚在所謂的犯罪構成之外。當然,在包含了主觀要素的情況下,塔甘采夫所說的犯罪構成與古典派犯罪論體系所主張的客觀的構成要件已經存在明顯區別。
將犯罪構成改造成為犯罪成立條件的總和,這是蘇俄學者完成的,其中特拉伊寧功不可沒。特拉伊寧把對于犯罪成立具有決定意義的各種主客觀要件都納入犯罪構成這一理論框架,對犯罪構成作出了以下界定:犯罪構成乃是蘇維埃法律認為決定具體的、危害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為犯罪的一切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因素)的總和。以上客觀要件包括客體,而主觀要件包括主體,因而形成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這四要件就是指: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這一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遂成蘇俄刑法學的通說。我國目前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從蘇俄引入的。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在整整20年的時間內,犯罪構成理論被打入冷宮。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我國法治重建,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重新登上我國刑法的學術舞臺。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以四要件為框架,完全是蘇俄犯罪構成的翻版,沒有任何變化。
經過蘇俄刑法學者的改造以后,構成要件轉換成為犯罪構成,而犯罪構成是犯罪成立條件的總和,甚至在犯罪規格的意義上使用犯罪構成概念。例如我國學者指出:作為犯罪規格的犯罪構成,是以刑法對構成犯罪必要條件的規定為存在前提的。只要有刑法(不論其表現形式如何),只要刑法規定了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不論是否完善),使之成為構成犯罪的規格,就有犯罪構成。由此得出的必然結論就是:只要存在刑法,就存在犯罪構成。因此,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存在犯罪構成。在犯罪規格意義上的犯罪構成,已經完全悖離構成要件這一概念的特定含義。因此,四要件的犯罪構成是沒有構成要件的犯罪構成。
二、如前所述,構成要件一詞是費爾巴哈引入實體刑法的,但真正在構成要件概念的基礎上建構犯罪論體系的,是德國刑法學家貝林。事實上,作為古典派的犯罪論體系的另一創始人李斯特,在其刑法教科書中并沒有把犯罪論體系建立在構成要件概念的基礎之上。李斯特雖然把犯罪定義為符合犯罪構成的,違法的和有責的行為。⑧但在李斯特的犯罪論體系中并沒有構成要件這一階層。李斯特是在犯罪的特征的名目下討論犯罪成立條件的,其犯罪成立條件分別為:(1)作為行為的犯罪;(2)作為違法行為的犯罪;(3)作為有責行為的犯罪。此外,李斯特還討論了可罰性的客觀條件,即客觀處罰條件。只是到了貝林,構成要件概念才發揮基石作用,以此建立犯罪論體系。⑨貝林的構成要件論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一)構成要件的指導形象功能
貝林認為,在構成犯罪的各種要素中,構成要件具有特殊的功能,它是一種觀念指導形象。這里的指導形象,是指構成要件具有決定犯罪性質的功能,并且其他要素都對構成要件具有依附性。貝林形象地把構成要件比喻為一個鉤子,指出:法官相當于有了一個鉤子,他可以把案件懸掛在這樣一個鉤子上面。因為,所有犯罪類型(獨立、直接的或者附屬、間接的)都離不開一個行為指導形象的法定構成要件。然后分別進行排除,即客觀方面的相關行為是否充足(Genüger)法定構成要件(一般稱為構成要件符合性)。這是由揭示犯罪形態而與構成要件建立聯系的問題,也即是處于優先考慮地位的問題。因為所有后續研究都有賴于該問題的解決,該問題本身相對于其解決的答案則具有獨立性。由此可見,構成要件相對于其他犯罪成立條件具有優位性,只有存在構成要件,其他犯罪成立條件才能依附于構成要件而存在。
(二)構成要件的類型性特征
犯罪本身是一種類型性的存在,各種犯罪都是一種犯罪類型。構成要件不能直接等同于犯罪類型。如果說,貝林在早期曾經把構成要件與犯罪類型劃等號,那么,在晚期貝林已經糾正了這一觀點。盡管如此,構成要件類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犯罪類型,因而構成要件是前置于犯罪類型而存在的。貝林指出:每個法定構成要件肯定表現為一個“類型”,如“殺人”類型、“竊取他人財物”類型等。但是,并不是意味著這種——純粹“構成要件”的——類型與犯罪類型是一樣的。二者明顯不同,構成要件類型絕不可以被理解為犯罪類型的組成部分,而應被理解為觀念形象(Vorstellungsgebild),其只能是規律性的、有助于理解的東西,邏輯上先于其所屬的犯罪類型。構成要件所具有的類型性特征,為犯罪認定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并且使其他個別性要素有所依歸,這對于定罪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三)構成要件的客觀性與事實性
在貝林的構成要件論中,構成要件具有客觀性與事實性。客觀性是與主觀性相對應的,貝林恪守“違法是客觀的,責任是主觀的”原則,將不法與責任加以區隔。在構成要件中只討論犯罪成立的客觀要素,至于主觀要素則在有責性中討論,那是一個如何對違法后果承擔責任的問題。事實性是與規范性相對應的,貝林主張構成要件是中性無色,不包含價值判斷的。價值判斷是在違法性階層進行的,因而使構成要件具有形式性。構成要件的客觀性,是貝林的構成要件論最遭人詬病之所在。此后,新古典派的犯罪論體系發現了主觀的構成要件要素,這主要是指主觀違法要素。而目的行為論體系完成了從心理責任論向規范責任論的轉變以后,將故意與過失這些心理要素從責任中分離出來,并將其納入構成要件,由此使構成要件成為同時包含客觀要素與主觀要素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貝林的構成要件論。(12)關于構成要件的性質,目前在刑法理論上仍然存在不同見解,主要包括以下三說:一是行為類型說,認為構成要件是形式性的、價值中立性的行為類型,并不具有違法推定機能、責任推定機能。二是違法行為類型說,認為構成要件屬于違法行為類型,因而肯定構成要件該當性具有違法推定機能。三是違法有責行為類型說,認為構成要件既是違法行為類型,同時也是有責行為類型。(13)在以上三說中,涉及構成要件與違法性、有責性之間的關系。貝林對構成要件的觀點屬于行為類型說,他嚴格地將構成要件與違法性加以區隔。而違法行為類型說則承認構成要件的違法推定機能,為此承認對于違法推定具有意義的主觀違法要素,但故意與過失仍然是責任要素,否認構成要件具有責任推定機能。而違法有責行為類型說則將故意與過失納入構成要件,使構成要件同時具有違法推定機能和責任推定機能。在以上三說中,我以為違法行為類型說是可取的,它堅持了違法與責任的界分,使構成要件的客觀性在一定限度上得以維系,因而更有利于發揮構成要件的機能。
應當指出,在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中,無論對構成要件作何種理解,它與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中的犯罪構成要件的概念都是完全不同的。但在蘇俄及我國刑法學對于構成要件的理解上,往往存在著混淆之處。其中,蘇俄學者特拉伊寧基于對構成要件與犯罪構成這兩個概念的混淆而對貝林的構成要件論的批判,是最為不堪的。例如特拉伊寧將貝林的構成要件論稱為犯罪構成的客觀結構,并作了以下批判,指出:這種人為地割裂犯罪構成的統一的概念的作法,以后得到了更進一步的表現。“犯罪學說”這一專著的作者別林格(指貝林,引者注,下同)提出了下面的一般原則:“凡是違法地和有罪過地實現某種犯罪構成的人,在具備可罰性的條件下,就應當受到相應的懲罰。”別林格把犯罪構成同那種作為犯罪構成而不具有任何主觀色彩的行為混為一談,使主體的抽象行為達于極限。別林格說:“犯罪構成是一個沒有獨立意義的純粹的概念。違法的有罪過的行為在形成犯罪構成后,就成了犯罪行為。犯罪構成本身存在于時間、空間和生活范圍之外。犯罪構成只是法律方面的東西,而不是現實。”犯罪構成是犯罪的無形的反映。這樣一來,別林格就把犯罪構成由日常生活中的事實變成了脫離生活實際的抽象的東西,變成了“時間、空間和生活以外的”一個概念。
在以上批判中,特拉伊寧是站在主客觀相統一的犯罪構成論的立場上,指責貝林人為地割裂了犯罪構成的統一概念。實際上,貝林的構成要件只是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的第一個階層,即使主張客觀的構成要件論,也不存在違反主客觀相統一的問題,只不過在有責性中討論主觀要素。至于特拉伊寧指責貝林把構成要件由生活事實變成了脫離生活的抽象的東西,恰恰是特拉伊寧混淆了構成要件與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之間的關系。例如貝林揭示了觀念印象與事實存在的疊加(Zusammenwerfung)的辯證關系,指出:“殺人”的觀念形象從與此相對應的真實事象中推導出來的。但是,一旦推導出來,那么邏輯上可以明確:該觀念形象不僅不同于其涵懾(Subsumierbar)的犯罪事實(Vorkommennisse),而且在該形象未出現于犯罪事實中的時候還保留著其內容。由此,構成要件作為一種法律形式的觀念形象,與該當于這一構成要件的事實是有所不同的。特拉伊寧把構成要件等同于犯罪事實,正好說明其不了然于構成要件的抽象性。因此,特拉伊寧對貝林的指責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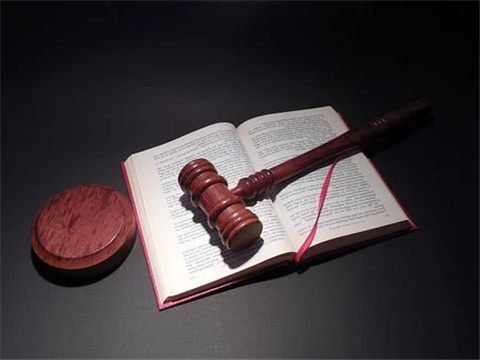
三、從內容與性質上來說,構成要件與犯罪構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德日刑法學中,盡管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經歷了復雜的嬗變過程,構成要件的內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動,但構成要件的概念仍然是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的基礎,這一點是不可動搖的。應該指出,刑法學中的構成要件具有特定的含義,它和一般意義上的構成要件是有所不同的。對此,日本學者小野清一郎指出:在這個時期(指19世紀,引者注),構成要件卻超出了刑法學的領域,被當做一般法學的概念來使用了,以致在哲學、心理學等文獻中,也偶爾可以看到這個詞。在一般法學上,則由于一定的法律效果發生,而將法律上所必要的事實條件的總體,稱之為“法律上的構成要件”。我國的民法學者,把它稱為“法律要件”。在刑法學上,犯罪的構成要件,其理論性只是它其中的一種情況——因為在歷史上,刑法中最早出現的構成要件概念是采用一般法學的思維方式得出的。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按照一般法學的用法,構成要件一詞僅僅意味著是法律上的、抽象的、觀念性的概念。與此相反,在心理學等方面,在使用“Tatbestand”一詞時,基本上是指事實性的東西。
在此,小野清一郎指出了刑法學中的構成要件與一般法學上的構成要件以及心理學上的構成要件的區別。心理學上的構成要件是事實性的概念,而一般法學上的構成要件是觀念性的概念。一般法學上的構成要件是發生法律效果的條件,而這一點與刑法學上的構成要件是有區別的。在刑法學的構成要件的演變過程中,存在一般的構成要件與特殊的構成要件。例如弗蘭克指出:所謂一般構成要件,是指成立犯罪所必需的要素的總和;所謂特殊構成要件,則是指各種犯罪所特有的要素。(17)但作為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之基石概念的構成要件,是指特殊的構成要件,或稱具體的構成要件,它是指刑法分則規定的具體犯罪的成立條件。對此,小野清一郎指出:構成要件理論中的構成要件,即是刑法各條中規定的“罪”,亦即特殊化了的犯罪概念。換言之,它就是特殊構成要件,而不是一般構成要件的意思。從一般構成要件——這個概念是否有必要存在也是值得懷疑的——方面來看,構成要件相符性,既要有符合構成要件的事實,這是它的一個要素,此外,再去考慮違法性和道義責任等問題。構成要件作為特殊性規定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法律上規定的概念,它又未免是抽象的、形式的,它與所有法律觀念一樣需要加以解釋。
在此,小野清一郎明確地把構成要件界定為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特殊的構成要件,它與犯罪成立條件總和的一般的構成要件是不同的。與此同時,貝林及其同時代人的著作中還經常使用一個概念:法定的構成要件。這里的法定,是指刑法分則對具體犯罪的規定,因而構成要件是以刑法分則規定為中心形成的一個法律概念。在刑法分則中對某一個具體犯罪的規定,通常是對行為等客觀事實的規定,只有在個別情況下規定了目的、意圖等主觀要素以及身份等主體要素。至于故意、過失、責任能力等對于犯罪成立來說具有一般意義的責任要素都是在刑法總則中規定的,因而不屬于構成要件的范疇,即使是主張違法有責行為類型說的小野清一郎在回答屬于一般責任條件的故意過失,是否也屬于構成要件這個問題時指出:在被類型化并且特殊化的限度內,是應當屬于的。這里所謂“被類型化并且特殊化的限度內”,我理解,就是指在刑法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
構成要件之所以必須是特殊的、以刑法分則規定為限的,主要是為了正確地實現構成要件的機能。在刑法理論上,一般認為構成要件具有以下機能:一是保障機能,亦稱為罪刑法定原則機能;二是個別化機能;三是違法性推定機能。(20)此外,經常論及的還有構成要件的故意規制機能和訴訟法機能等。
(一)構成要件的保障機能,要件的保障機能是指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律明文規定是通過在刑法分則中設立構成要件完成的,因而構成要件是罪刑法定原則實現的保障。正如我國學者指出:
在現代刑事立法中,對于犯罪的處罰除了在刑法總則中規定一般要件以外,在刑法分則中更是對各種具體的犯罪設置了相應的構成要件,這已經成為現代刑事立法技術上的特色。這顯然是為貫徹罪刑法定主義,應其明確性要求而為的。因此,正確地理解構成要件的概念,對于正確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則是具有直接關聯的。基于罪刑法定原則的立場,對于開放的構成要件等理論都要保持足夠的警覺。
(二)構成要件的個別化機能
構成要件的個別化機能是指通過構成要件將此罪與彼罪加以區分。當然,客觀構成要件論對于個別化機能的實現是有限的,如果把故意或者過失納入構成要件,就會使構成要件的個別化機能大為提升。例如,如果限于客觀的構成要件,則殺人罪、過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在構成要件階層是無法區分的,這也正是反對客觀的構成要件論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認為構成要件的個別化機能不是絕對的,對于大多數犯罪,通過構成要件該當性這一階層,就可以實現犯罪個別化。但對于少數犯罪來說,雖然在構成要件中不能實現個別化,但經過有責性的判斷而實現個別化,這是一種分階段地個別化。盡管如此,在構成要件階層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個別化機能。
(三)構成要件的違法性推定機能
構成要件的違法性推定機能,這是違法行為類型說所具有的。因為構成要件的內容是刑法禁止的行為,實施構成要件的行為在通常情況下都具有違法性,除非存在違法阻卻事由。即使是在形式的構成要件論中,由于構成要件具有違法性推定機能,也使構成要件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實質的違法性。在目前的構成要件中,包含了以客觀歸責為內容的實質判斷,因而其所具有的違法性推定機能更為明確。
(四)構成要件的故意規制機能
構成要件的故意規制機能,是指凡是構成要件要素都是故意所認識的客體,從而限制或者決定了故意的內容。關于構成要件的故意規制機能,以往我國刑法學界重視不夠。當然,在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中,根本就不存在構成要件的故意規制機能。對于故意規制機能,日本學者指出:犯罪原則上必須出于故意,但是,由于故意的內容是對符合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的認識和實現的意思,因此,在結局上,決定成立故意所必要的事實范圍的還是構成要件。構成要件具有規制故意內容的機能。這一機能被稱為故意規制機能。構成要件的故意規制機能是構成要件的類型性特征,為具有個別性判斷性質的故意認定了某種范圍,對于正確地理解故意的內容具有重要意義。構成要件的故意規制機能昭示了以下原則:凡是構成要件要素都是故意所應當認識的,沒有這種認識也就沒有與構成要件相關的故意。因此,在奸淫幼女的情況下,幼女年齡屬于構成要件要素,當然是故意所應當認識的內容,沒有這一認識也就不能成立奸淫幼女的故意。此外,對于身份犯來說,主體自身的身份也是故意認識的內容。
(五)構成要件的訴訟法機能,構成要件的訴訟法機能是指構成要件是刑事訴訟中的指導形象,它對于確定訴因、管轄、證明都具有重要意義。對此,日本學者小野清一郎曾經作過詳盡的分析,在此不贅。
四、蘇俄學者創立的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是以犯罪構成為中心的。如前所述,這一犯罪構成是指犯罪成立條件,因而在犯罪構成中已經看不到構成要件的蹤影,構成要件所具有的特征與機能也蕩然無存。在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中,定罪的過程分為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與有責性這樣三個步驟,依次遞進,因而構成要件的內容是較為單純的,即使在目的行為論出現以后,構成要件的內容雖然大為擴張,但仍然局限于事實性的內容。但在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中,犯罪構成承載了事實與價值、主觀與客觀、形式與內容等各種犯罪成立要素。這樣一種犯罪構成概念,正如我國學者所說是一元化的、閉合式的犯罪構成。這一犯罪構成具有以下特征:
(1)犯罪構成是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的統一;
(2)犯罪構成是事實評價和規范評價的統一;
(3)犯罪構成是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的統一;(4)犯罪構成是形式違法性與實質違法性的統一;
(5)犯罪構成是客觀危害與個人責任的統一;
(6)犯罪構成是評價過程與評價結論的統一。將這么多的內容統一于犯罪構成,必然帶來消極后果。
對犯罪是否成立的評價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工作,犯罪構成絕不等于各項要件的簡單羅列,犯罪評價不是搭積木之類的游戲。四大構成要件相加,可能得出行為成立犯罪的結論;但也可能得出其他的令人難以接受的其他結論,部分之和并不是隨時都等于整體。這是需要我們警惕的事情。
本來,構成要件是認定犯罪的一種“抓手”,借助于構成要件可以對犯罪成立的各種要素起到一種綱舉目張的作用。但當構成要件被改造為犯罪構成以后,各種犯罪成立要素“一鍋燴”,消解了構成要件的機能。其實,蘇俄學者特拉伊寧在改造構成要件過程中,在其犯罪構成體系的背后隱約地存在構成要件的影子。例如,在論及犯罪構成的因素時,特拉伊寧曾經指出:在著手解決這個復雜的任務——犯罪構成因素的分析和分類——之前,必須限制一下它的范圖:必須指明,哪些情況,盡管它們對于負刑事責任說來絕對必要,但不能認為是犯罪構成的因素。應當指出這種情況有兩類:(1)表明主體本身的情況;(2)表明主體行為的情況。
這里的表明主體本身的情況,是指刑事責任能力。特拉伊寧認為責任能力并不是犯罪構成的因素,也不是刑事責任的根據。責任能力通常在犯罪構成的前面講,它總是被置于犯罪構成的范圍之外。這里的表明主體行為的情況,是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特拉伊寧認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都是決定每個犯罪構成的基本的、本質的屬性。但社會危害性不是犯罪構成的一個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是犯罪構成的因素呢?特拉伊寧指出:為了理解犯罪構成因素的性質,必須注意下面一點:只有法律賦予它刑法意義,并因而列入分別規范罪狀中的那些特征,才是犯罪構成的因素。
聯系到特拉伊寧關于“罪狀是每個構成的‘住所’”的命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種由刑法分則的罪狀規定的犯罪構成因素不正是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中的構成要件嗎?責任能力屬于責任問題,不是在構成要件中討論的,至于犯罪主體中討論的是特殊主體,也就是身份犯之身份問題。而社會危害性作為對構成要件的實質判斷也不是構成要件的具體要素,而是在違法性中討論的。至于正當防衛、緊急避險這些屬于排除社會危害性的情形,按照特拉伊寧的邏輯,當然也不在構成要件中討論。顯然,這樣一種具有構成要件性質的犯罪構成概念與作為犯罪成立條件總和的犯罪構成概念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邏輯。我國學者把特拉伊寧的觀點稱為二元的犯罪構成論,指出:在作為刑事責任根據的廣義的、實質的犯罪構成概念和分則特殊的、法律的、狹義的構成要件概念之間,是特拉伊寧在西方三要件論與蘇俄刑法傳統和制度上左右搖擺的表現之一。可以說,特拉伊寧經歷了一個從三階層到四要件的艱難而無奈的轉變。特拉伊寧的《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一書根據蘇俄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歷經三次修改,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發現貝林的構成要件論的蛛絲馬跡。
在此后蘇俄刑法學與我國刑法學的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中,特拉伊寧的狹義的犯罪要件的陰影也被消除,構成要件被徹底改造成為犯罪成立條件總和,它是對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的犯罪成立條件的一種抽象。我國目前有不少學者都對這種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體系進行了批判,并且提出了各種重構我國犯罪構成體系的思路。在這些思路中,除了對四要件進行簡單的排列組合的觀點以外,一種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觀點是以罪狀為中心重建構成要件論,為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提供支撐。例如我國學者阮齊林教授認為應當把犯罪表述為該當罪狀、違法、有責的行為,由此建立一個模仿三要件論的體系。阮齊林教授在論述罪狀論時指出:首先以行為觸犯刑法罰則即該當分則條文的罪狀為犯罪的第一要件。在此,重要的是把罪狀(或通過分則罪狀描述的因素)當作一個整體掌握,作為犯罪構成論的核心。在罪刑法定的制度下,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三要件論中,稱其為“構成要件”。在法國理論中,稱其為“法定要素”,在英美理論中,稱其為“犯罪定義”。犯罪構成的一般理論應當以此為中心展開。
應當說,阮齊林教授在犯罪構成體系中直接引入罪狀的概念,強調犯罪構成的第一個要件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罪狀,在一定程度上還原構成要件論,是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此外,李立眾博士構筑的德日式犯罪成立之路,基本輪廓是罪狀符合性、不法性與罪責性。其中,以罪狀符合性為內容的是罪狀符合論。然而,李立眾博士強調罪狀是一個總則性的刑法概念,以此發揮罪狀的機能。但從所列機能來看,都是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中構成要件的機能。這樣,就使我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不徑行恢復使用構成要件一詞,而是要采用罪狀一詞?對此,李立眾博士從三階層論核心術語的本土轉換的角度進行了論證,主要理由是德語中的Tatbestand一詞本身為“行為情況”之義,并不含“要件”或者“要素”的意味,如依漢語,毋寧稱之為“構成事實”;日本用語乃謂之構成要件,不但文字與原意頗有出入,且易生誤解。
這里的誤解是指與犯罪構成或犯罪構成要件混淆。我認為,構成要件一詞已經約定俗成,只要從犯罪構成中將其復原即可,沒有必要改稱為罪狀。罪狀雖然屬于刑法分則性規定,與構成要件的性質接近。但罪狀引入犯罪論體系,存在一個重新適應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將構成要件改為罪狀以后,無法與德日刑法學相銜接。如果構成要件改為罪狀,是否以后翻譯德日刑法學著作也一并將Tatbestand譯為罪狀?而德日刑法學中,除犯罪論體系中的構成要件一詞以外,其刑法分則中都有罪狀一詞,那么,這兩個罪狀如何區分?這些問題不解決,會在對外學術交流上徒添障礙。不如直接采用構成要件一詞,對構成要件重新解釋,將它從四要件的犯罪構成中解放出來。 上海黃浦刑事律師事務所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